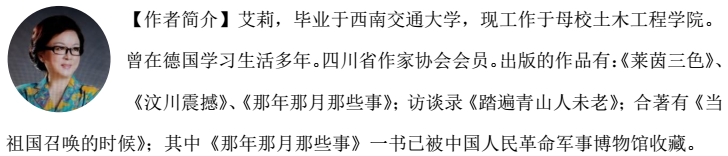
小序
2018年2月25日噩耗传来,463永利官网麦倜曾教授去世了,享年93岁。他是对中国隧道与地下工程学科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专家。他喜欢音乐,三年前我去他家采访,他还为我弹奏了三首著名钢琴曲,送了我一本音乐小册子。那个下午,有阳光,有琴声,有我的掌声,有他神采飞扬的讲述,至今仍历历在目。
2004年麦倜曾教授八十大寿时,王梦恕院士在祝寿信中写道:“他精辟地总结当年隧道工程的落后,带着感情描述隧道工人的艰辛和危险,又充满希望预见隧道和地下铁道发展的宏伟蓝图,鼓励有志之士应投入到这个专业中去,并殷切地给予众望,他呼吁祖国的需要就是青年学生的志向。我在麦老师动情的讲课中建立了隧道事业奋斗一生的信念。”
这即是学生对恩师发自肺腑的高度评价,又是麦倜曾教授高风亮节执着于教育事业真实写照。
安息吧!麦教授。愿天堂有钢琴、有乐谱、有唱片,在美妙圣洁的音乐里,您的灵魂得以安息。

(2016年校庆期间麦倜曾教授正在发言)

春雨润物细无声
——专访麦倜曾教授
麦倜曾教授给我的第一印象:严谨;第二印象:很严谨;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麦倜曾教授都是师生心目中的典范。他不仅治学严谨,而且为人正直坦荡,爱憎分明。他热爱教育,热爱学生,是一个以严谨著称、德高望重的人。
一
麦倜曾教授学养深厚,做人严谨,他喜欢独立思考,并于细微之处见精神,于细微之处见境界,于细微之处见水平。他说古人云:“心要有城池,口要有门户。有城池则不出,有门户则不纵。”“敏于行而慎于言”。
三年前,我向麦倜曾教授请教写作史志方面的问题,他说:就他这一代人来讲:
第一,写个人经历:1、点出解放初期国家经济困难情形,现在总有人认为港台建设得好,咱们不成,这些人根本不知道解放时我们接受的“烂摊子”是什么样子,写史料就要实例,告诉现在和以后的国人,建国初期中国如何“高楼万张平地起”,对现在的各种“败家子”会起点作用。2、用那个年代的生活、学习、工作的实例,告诉人们当时社会风气、关系、规范等等,使人们知道雷锋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是有社会、经济、文化等等基础的,从而对恢复社会好风气增加信心。
第二,写专业创建史要对事不对人,写白手起家,从无到有的奋斗过程,例如交大,1952级隧道专修科、隧道专业课(课堂和现场的上课、实习、设计)的开设,把隧道专业桥头堡的建立情况如实反映出来。历史是没办法“重来一次”的,能走过来就是胜利了,但不见得会尽如人意,如果能再来一次,“我将如何如何?”那是“马后炮”,没法实现的空谈,不过由当事人反思反思,也许对后来者还有点启发作用。
第三,在写作上要不打妄语,求真求实,每一件事的阐述,要么有人证,要么有文件,不能凭空想象,不能过度夸张,让事实说话。
二
麦倜曾教授是永利463官网知名教授,我国隧道工程设计资深专家,我国高校铁路隧道专业的创建者之一,他长期致力于铁路隧道、山岭隧道的教学科研工作。他秉承严谨治学的传统,在传道、授业、解惑的过程中严密谨慎、严格细致。他努力钻研业务,不断学习新知识,探索教育教学规律,改进教学方法,提高科研水平。他说,严谨就是要求教师要多学、多思。孔子云:“学而不思则罔。”多思是教师的基本素养之一。因此,麦教授告诫学生:学习中多一点思考,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养成严谨求学的好作风。
麦倜曾教授热爱并忠实于自己的师者职责,从他的工作经历中不难看出:师者生涯几十年。
1.1949年3月至1950年3月在在铁道部工务局工作,期间曾于1949年6月至9月参加铁道部津浦线调查队,在战场组工作;
2.1950年4月至8月在太原铁路局工务处工作,其间主要参加铁道部设计局北同蒲改线测量队工作;
3.1950年8月至1951年7月在临汾铁路局工务科工作;
4.1951年7月至1952年6月在铁道部东北铁路学院学习(教研班);
5.1952年6月至8月在东北铁路学院土木系工作;
6.1952年8月至现在永利463官网(唐山铁道学院)工作。
麦倜曾教授自1952年8月以来一直致力于隧道学科的创建、发展、壮大、繁荣的工作。他勇于作为,孜孜以求,不求名利,甘当人梯。建国初,他协助高渠清教授创建了全国第一个隧道专业;主编、主审过本科教材多种;兼任过《土木工程学报》编委等职务;1982年起招收研究生;1985年任学校出版社总编辑;曾出版过编、译书15种,科技论文8篇,其中合译的苏联版《隧道》,解决了1953——1955年隧道专业教材急需问题;1961年于他人合编的《山岭隧道》是全国隧道专业第一本中国专家的自编教材;曾有两篇论文被国际会议采用为大会论文。
麦倜曾教授总结自己的工作,概括为:
1、在高渠清教授成立隧道教研室之前,他与关宝树同志从1952年开始从无到有地开出“隧道设计”“隧道施工”课,完成了除毕业设计以外的全部教学环节的“首演”(debut)。除讲课和实习之外,他着重主持了苏联教材的翻译与隧道模型的制作。在这前期两年工作中,1953年秋增加了谢锦昌与赵子荣两位生力军,他们共同努力送走了本专业的第一班(隧道专修科)学生,这批学生正赶上第一个五年计划,成为宝成铁路和其他几条新线路的隧道设计与施工的急需人才,做出了可喜的贡献,其中如王效良、姚成惠、刘茂桑等都成为我国隧道界知名人士。
2、在1955至1956年试做了隧道毕业设计,通过铁道部组织的专家答辩,为后来毕业生综合水平的提高铺平了道路。
3、在“文化大革命”后期,铁道部西南研究所主办的《隧道译丛》复刊,当时条件困难,主编傅炳昌向本校求援,我为其译稿,还做了大量的文字润色与译名规范化工作,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硬逼老傅把“那瓦约”改为“纳瓦霍”“艾伯特;马修斯”改为“阿尔玛.马蒂厄”,使杂志不但存活下来,而且质量得到读者的认可。做这些工作,当时既无署名也无稿酬,是“杨白劳”。
4、在我国理工学院的教学中,率先开设了音乐选修课,以提高大学生的美学素养和综合素质。
5、所做的关于铁路隧道、山岭隧道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对我国铁路隧道前期建设工作均具有开创性作用,为我国铁路隧道、山岭隧道的理论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6、1990年退休,聘任为永利463官网出版社顾问。期间,严把质量关,编过一些书,其中编辑《艺术国宝》(在加拿大发行的Art Treasures in China,作者为梁明任女士)一书最为辛苦。为编辑此书,他学习了大量的陶瓷、青铜器、雕塑、书法、国画、艺术特点和价值等方面的知识,为《艺术国宝》一书锦上添花。
三
麦倜曾教授自1952年起在西南交大(唐山交大)工作生活一个甲子还多好几年。90岁时仍然风趣幽默,侃侃而谈他的童年、青年时代,神采飞扬,他回忆说:
(1)
1924年5月生于北京,祖籍广东顺德人。父亲麦公立,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律专业,学成归国在北京法院任职,曾当过律师;母亲麦清水;麦倜曾在家里排行老五;1930年在北京上的小学。小学读了半年,父亲调到青岛工作,原因是当时青岛法院有许多和日本人打交道的工作,父亲从日本留学回来,法院就请父亲去任职。当时母亲身体不好,于是举家迁往青岛。在北京读小学一年级时,觉得学的东西太浅,到青岛后连跳两级,直接入三年级读书,因为上学之前,大哥就教过其算术,背诵了小九九表。我家附近有一个电影院,电影是滚动放映。夏天青岛很热,电影院一到晚上就敞开太阳门通风,于是我们几个玩伴就从太阳门钻进去看免费的电影,一场接一场。从1931年至1937年,是我在青岛度过的最美好的六年时光。1937年青岛沦陷前,政局动荡不安,当年11月父亲通过关系把家人迁移到香港。当时父亲要处理一件国家大事,所以没有和家人一起赴港,这在当时是冒着很大风险的,生死未卜。父亲临行前要把青岛法院掌管在他手中的一批数额很大的余款汇入国民政府,此举得到了国民政府的通报表扬,称赞父亲保全了国民政府的财产,没有把国民政府的钱留给日本人,这也是父亲没有同全家人一同赴香港的原因,因为父亲不能让国家财产落入日本人手里,必须处理好这笔资金才能撤离。没多久父亲也过来香港和家人团聚了。父亲一直有个担忧,中日战争开始了,他是日本大学毕业的,怕被抓去当汉奸,于是全家只好逃难到香港。在香港的日子里,父亲怕被日本人认出来开始蓄胡须,隐姓埋名躲在家中很少外出。逃难到香港初期,我辍学在家,直到1938年才开始上初中。在北京和青岛时,听父亲和叔伯们讲广东话,能听懂,但不会说,到了香港必须要说广东话,所以一家人都学说广东话。1941年日本偷袭了美国珍珠港,香港12月中旬开始沦陷。当时有一个远房亲戚在香港开银号,香港被占领后日本人天天来银号纠缠,亲戚只好把隐姓埋名的父亲请出来当翻译,父亲在尴尬中只得去帮忙。在香港我家住九龙,我在九龙读中学。香港读书期间,庆幸学到了很多东西,影响深远,一生受益。国难当头,民不聊生,当时内地很多学校要么搬迁,要么停办,许多大学老师逃到香港避难,所以教我的那一大批老师很多都是大陆来的,有着很好的才学和很高的操守。其中印象最深的一个老师叫陈智乐,教代数,所留作业批改后,发作业本时陈老师要把学生一个一个叫上去谈话。当叫到我时,老师一边把作业本给我一边问:“你学过吧?”我说:“没有。”“我看你的作业做得很好。”老师的一句话,我信心倍增,以后在上这门课时特别用功,认真听讲,认真做作业,这门课学得最出色。英文的老师叫黄薄天,英语很棒,原来在北京税务学堂学习海关税务,后来在税务局工作,因为当时税务局总税务司是英国人,要求工作时讲英语,公文全是英文。战争期间黄老师来香港教书。黄老师得知我参加了学校业余合唱团,合唱团活动很多,于是就把我的擅长和英文学习结合起来。当时英文课中有一篇课文是讲《贝多芬的夜光曲》也有人称《贝多芬和盲女》。于是黄老师宣布:“下周《贝多芬的夜光曲》由学生上课,学生老师就是麦倜曾。由于我的音乐常识很少,而麦同学的音乐知识比我丰富,所以麦同学主讲。学校从未有过学生当先生的教学模式,学生们起哄、期盼;我紧张、积极,既然黄老师安排了,我就拼命地准备。到了上课的时候,我勇敢地站到了讲台上。我在上面讲,黄老师站在台下听,有补充的地方黄老师就补充。这一课非常轰动,连校长都知道了,记住了“学生老师”叫麦倜曾。
当时学校为社会下层穷困家的孩子办了夜校(即晚上上课)。校长听说我讲课不错,当师资不足时,校长就问我愿不愿意给夜校的孩子上课,当时晚上也没有什么事,我就一口答应了校长,做起了夜校“老师”。后来我又干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渐渐地我讲课越来越娴熟。我的教师情结可能就是那时萌芽的。
1942年,父亲的一个朋友,原来在天津开银行的,经常需要和日本人交涉事务,邀请父亲去他的银行工作,于是8月底9月初全家迁回天津,居在法租界里。为搬迁我的学业又耽误了一年。全家搬到天津后,我在天津工商大学附中上学,那是一所法国天主教会办的学校,我直接插入高二班学习。这所教会学校,对工程教育很重视,对商科的课差些。当时学生们要买图版,丁字尺,学工程制图。神父中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他们劝学生信仰基督,说信仰了基督教,将来功课好可以到外国留学。
(2)
1944年高中毕业,准备考大学,学校欲保送我上工商大学,可我不喜欢,于是凭着实力考取了北大土木工程专业。1944年9月入学,战争年代,北大很乱。第二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接收了学校。当时学校调整,学生们可以自由选择是继续留在北大,还是转入北洋大学。我选择留在了北大,有一半同学去了北洋大学(在天津)。我的同学严宗达去了北洋大学,后来成为赫赫有名的塑性力学大师;俞敏也去了北洋大学,他搞氢弹研究时隐姓埋名,不能发表文章,不能得奖励,一切均在保密状态,现在是中国的氢弹之父,后来江泽民奖励20几名氢弹专家时,就有俞敏的名气。当时北大印象较深的任课老师有桥梁专家金涛老师,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在美国时就加入了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ASCE),金涛是正式会员,金涛老师在北大任教我们《超定结构力学》,讲课非常民主,有不懂的地方学生就提问,有不对的地方学生要当场指出来。记得有一个同学叫张家昭,跟老师联系非常多,走得很近,有一次在课堂,金老师把运算符号“+”“-”弄错了,张家昭立刻站起来:“金老师,符号错了。”金老师当场一愣,仔细看了一下试题,连连地说:Thank you!Thank you!金老师的课难学,只有很少的几个学生能跟上老师的思路。张家昭毕业后去了台湾。另一个印象深刻的老师是张泽熙老师,张老师先在清华大学当老师,后被聘请到北大土木系当系主任。张老师讲授《铁道工程》和《选线》,讲课特点:专用名词全是用英文,所以学生毕业去现场很不适应,现场如何叫不知道。1952年中国大学院系调整,张教授来到了西南交大。一次在路上,我见到张教授,他对我印象很深,聊的很融洽。张教授说:“听说你在铁路现场干过几年,怎么样?”我说:“你教专业术语都是英文的,到现场很不适应,只好在现场再学中文名词。”张教授让我举个例子。“mine(地雷)这个东西的叫法最深刻。mine学名叫‘响墩’,巡道工跟它叫‘王八’(俗名),‘王八’和动物的‘王八’形状很像,用于铁路出现故障临时为列车预警用的。巡道工发现某段线路出现问题,就在故障地很远的铁路上放一个‘王八’,列车通过时会轰地炸响,司机就马上刹车。”张教授听了mine,哈哈大笑,连连称赞:“孺子可教也!”、“孺子可教也!”那时师生关系很好,知无不言。还有一个徐愈老师,讲授《桥梁隧道工程》,他讲课善用启发式教学方式,启发学生想象力,给人印象深刻。开始第一堂课讲概论,徐教授概述地介绍了桥梁的各种形式,各式各样的桥,然后给学生留了一个作业:给了一段河流的跨度,让学生选一个合适的桥放在上边架起。于是同学们忙了起来,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为“桥”而忙,兴趣极浓。你选这样桥,我选那样桥,同学们都把自己认为合适的桥画了出来。一个叫刘振宗的同学,贪玩忘了写这个作业,知道上课时要交作业,开始慌里慌张,看到同学们把桥都画好了,他就临时抱佛脚,草草画了一张图交上了,同学们都在取笑他。下一堂课老师的开场白:“你们的作业,我都看了,最让我佩服的学生有一个,他的想象力很丰富。”同学们屏住呼吸,盼望老师能报出自己的名字。“张振宗”听完老师宣布,大家万分意外。老师把张振宗的作业画在黑板上,指出想象力,同学们哈哈大笑,原来张振宗画的桥两边是气球。
提到想象力,我还有一个杰作。1948年春假时,同学中调剂去北洋大学的那部分人要来北京和同学搞联欢晚会,有晚会就要有节目,临时怎么排演呐?我灵机一动想出一档节目,找来8个人自由唱,每人唱一段自己最熟悉的歌或戏,我指挥:我一挥手,第一个人就开始唱,一个接一个,最后我再一挥手,就停。八个人有的唱京剧,有的唱小调,有的唱流行歌曲,我唱的是《我的太阳》,还有人唱的是《团结就是力量》,没想到这个节目特别火,大家还没欣赏够就戛然而止,得到的掌声最热烈。后来师大音乐系的一个同学见到我提到那次联唱,很惊叹,问我是如何想出来?很有创意。我的总结是:“创意创新有时都是被逼出来的。”
四
麦倜曾教授说:“我们西南交大被誉为隧道工程的摇篮,是名副其实。1952级隧道专修科是隧道教研室培养出来的第一期专业学生,毕业生大部分分配到全国各设计院和施工单位工作,他们学到的新知识和新技能对我国铁路隧道工程的发展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有些同学成了这方面的专家。王效良一直在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工作,他成为了隧道定型设计方面的“活字典”,在隧道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姚成惠在铁道部第二设计院的被尊称为“姚明洞”;刘茂燊被尊称为“刘通风”。他们因精通隧道某一领域的内容而被人用专业术语尊称。施仲衡、王梦恕是我们隧道专业培养出来的两位工程院院士,史玉新是设计大师,他们都是我们隧道专业的高材生。”
麦倜曾教授说:“有些事忘不掉,刻骨铭心。”
1、1950年8月至12月在临汾铁路局工务科工作时,参加调查南同蒲线全线桥涵养护情况,因为当时太原局条件艰苦,整条南同蒲线连一台押道车都没有,整个510km行程,调查任务都是步行完成的。那时参加测量队外业工作,怕点树枝烤馒头引燃山火,中午就啃冷馒头吃。
2、带学生实习,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去的地方多是“连鸟儿都不去”的荒山野岭。
3、1953年秋,率先为学生开出隧道设计和隧道施工两门专业课,当时一是没有教材,二是教具。他与关宝树老师一方面翻译苏联资料,编写讲义和教学文件,另一方面抓紧时间去现场实习和收集资料。他们自己设计和制作的教学模型十分成功,当时给隧道专业同学讲课用的全套模型都是他亲力亲为设计的。一次,他请一位能做精致家具的刘师傅制作模型,他只能靠手势说明模具的平、立、侧三面投影图,刘师傅就把我想象中的模型造出来。那时学校中电话甚少,上班时间找人困难,所以刘师傅经常在午饭时间到单身宿舍找我,我每次都是放下碗筷就跟刘师傅上木工房,当场商讨模型制作的问题。其中最能显示我们创意和刘师傅高超技术的模型是一台1:4的盾构模型,它造型逼真,在支撑环的整个圆周空间安装了24台盾构千斤项,其带有靴座的顶杆可用手动显示伸缩动作,学生一看就清楚盾构推进的原理。这台模型反映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际水平,多年来对培养地铁人才起到了重要作用。
4、1955年,隧道班的毕业设计没有老师指导,于是我上半年收集和整理资料工作,下半年搞毕业设计的试做。1956年初,毕业设计成型,同年2月1日,我随学校代表团赴沪,参加高教部在同济大学召开的铁道、桥隧、道路专业毕业设计经验交流座谈会。回校后,我对设计做了局部补正,25日进行了答辩。答辩委员会由铁道部组织,主任委员为铁道部第四工程局(当时正负责丰沙线施工,该线隧道很多)欧阳诚工程师,我们苏联专家雅科夫列夫担任顾问,委员有铁道部工程总局专家赵连甲工程师、高渠清教授等。我答辩前很紧张,当时一位同事递我半杯“味美恩”饮料,喝下之后镇定许多,鼓起勇气走入考场,结果以优异成绩通过了这份试做的毕业设计答辩。真是备感欣慰。
5、1962年隧1958班地下工程课程考试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地下结构属于超静定结构,计算比较繁杂,为缩短计算时间,我将结构的计算图示由教科书采用的正1 6边形简化为正8边形,使计算量大为减少,本以为这样一来,可简化对该题的计算,谁知这一变化反而难住了学生,全班只有王建宇和李荫广两位学生做了出来。王建宇是杭州入,一向以思维敏捷著称,事后我问此事,他说“这题目比教科书的例题容易得多,但我没有能一眼看出来,这说明平时看的书太少了。”之后他更加博览群书,成绩比以前更加突出。1963年秋王建宇毕业,分配到铁道部科研院,在该院例行的新人入职考试中,他的高等数学和外语考了第一名,使交大声誉大增。王建宇曾任铁科院西南分院院长,直到退休。李荫广是唐山人,是学校有名的撑杆跳运动员。他说见题目与例题不同,有点奇怪,但没有发慌,经冷静分析比较,发现二者原理相同,于是很快做了出来。他认为这种考题出得非常好,对每个人都是一种锻炼,从中可以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他毕业后到铁道部第三设计院工作。20世纪70年代他在第一总队工作时曾自己动手制造了一台碳粉复印机,当时美国施乐牌复印机刚在我国市场上出现,售价高昂令人咋舌,而李荫广这台简单实用的复印机只用了2000元,此举为我国在弱项上争得荣誉。李荫广后来多次出国做外援工作,曾任第三设计院副总工程师。
6、1977级隧道班的《专业英语》是我主讲的,为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在教学方法作了改进和创新。我认为在课堂上互换师生角色的做法是一种比较可行的方法,专业英语教学中,请学生讲课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因为三年级的学生已学完了《大学英语》,并已具备了相当建设工程的知识。有了这样的背景条件,在课堂上让学生讲课,再由老师把关,做必要的补正,其效果只会更好。上课采取由学生依次讲一段(长)或两段(短)课文,然后由我做出评价和指正,这种方式使学生课前主动预习,课堂上气氛活泼,有时还能展开小型讨论,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学生反映收获较大,最后期终考试普遍取得了较好成绩,全班仅有一位同学不及格。事后才了解到这位学生在东北农村上中学时,因地方太穷苦,请不到外语老师,在中学未学过外语,所以期终考试没考及格情有可原。如今这位校友在辽宁朝阳工作,是位独当一面的工程师。
7、我喜欢欧洲古典音乐,曾经因为聆听欧洲古典音乐把粥熬糊了;曾给学生开过几次“音乐欣赏”选修课。1979年,我建议由我主讲开设“欧洲古典音乐欣赏”选修课,得到了常务副校长沈正光和教务长王刚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学校电教室及该教室韩立平等几位年轻同志的大力协助,为该课程提供了全校最好的音响设备。“音乐欣赏”课时,峨眉山脚下飘荡起巴赫严谨且浪漫的复调音乐、贝多芬辉煌且奔放的交响曲,音乐使年轻人热血沸腾,使年长者增加音乐修养。课堂上最大的学生是任郎教授,时年65岁,每次可他必提前到,以便找一最好位置来录音。有位学生曾对我说:“贝多芬的艾格蒙特序曲给我勇气,使我一往无前,现在每当进入考场之前,我都要默哼一遍‘胜利进行曲’的旋律。”由于反应热烈,次年,音乐课又开了一次,为使学生能学点乐理知识,我把时间分出一半来讲乐理,课程名称也就改为“乐理及欣赏”。这两次选修课的开设,是我国理工学院较早的两次大胆尝试。后来我见到来峨眉开会的学长,大连理工学院结构专家唐立明授,他对我开设音乐欣赏课大为赞赏。1986年,某高校一位音乐专业研究生,到四川用抽查的办法调查个高校音乐普及程度,发现在峨眉山沟中有一所永利463官网,其学生的音乐水平竞高于其他城市中的高校,就以《可喜的倾向》为题在当年第14期《北京音乐报》上加以报导。我读后给该报写了回应如下:“贵报今年第14期第三版< 可喜的倾向>中举我们为例说明当代大学生的音乐欣赏活动在逐步倾向高层次”,看后高兴之余还希望能补充一点:即这种倾向是经过教育的结果,我们在79、80及85年各开过一次全校性的选修课(包括‘欧洲古典音乐欣赏’、‘乐理及欣赏’等)。选课的学生非常踊跃,听课的效果很有说服力:不少学生把原来录制流行歌曲抹掉改录交响乐、协奏曲,甚至有录西方歌剧的。因此我们希望全社会都注意对青年引导和教育。”该报在第16期(1986年8月25日)第三版全文刊载了此回应。我以前一直希望学校能多开设一些高雅的艺术课程,不应当搞太多商业化、低俗玩意儿。现在仍然是这种观点。
2011年元旦,77级毕业三十年返校纪念活动,当年的隧道学生们见到麦倜曾教授特别亲切,高度赞誉麦教授:教师育人的典范。
来源:463永利官网